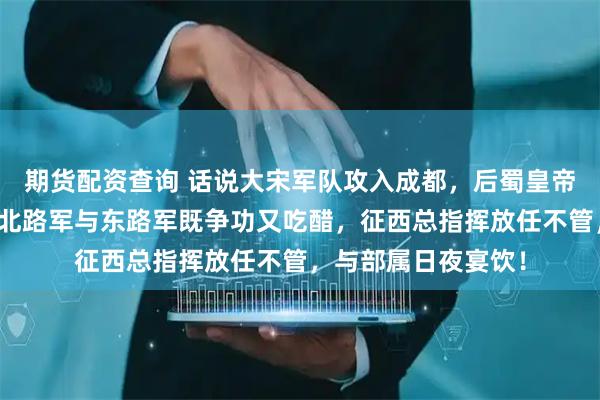我攥着那枚烫金请柬站在宴会厅门口时,水晶灯的光正晃得人眼晕。红色卡纸边缘还留着机器裁切的毛边,新郎栏里“陈默”两个字力透纸背,而被邀请人那一栏,“林溪”两个字像淬了冰,硌得我指腹发疼。
伴娘突然从后面勾住我脖子,婚纱裙摆扫过脚踝时带着香氛味:“你可算来了!刚还跟阿月说你是不是要逃婚——”她话说到一半突然卡住,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请柬上。空气里的香槟气泡声仿佛瞬间炸开,我看见她瞳孔地震似的放大浙江配资门户网,“这……这请帖是陈默亲手送你的?”
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。三天前在公司楼下便利店浙江配资门户网,陈默穿着灰色西装站在冰柜前,手里捏着两罐可乐。看见我时他喉结动了动,从西装内袋掏出这个红本本:“下周六,我和阿月。”阳光透过玻璃门斜切在请柬上,把“林溪”两个字照得像血渍。
宴会厅突然安静下来。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从旋转楼梯下来,头纱上的碎钻比星星还亮。我盯着她婚纱后领露出的珍珠项链——那是三年前我和陈默逛珠宝店时,他说“以后要给我新娘戴”的那一款。司仪开始念誓词,阿月的声音带着哭腔:“我愿意。”轮到陈默时,他顿了两秒,目光越过人群直直撞进我眼里。
“我愿意。”
这句话像根针,猝不及防扎进我太阳穴。三年前在出租屋楼下,他也是这样看着我,手里攥着褪色的电影票根:“林溪,等我攒够首付就结婚。”那天的风把他白衬衫吹得鼓起来,像只挣扎的鸟。后来他升了职,应酬越来越多,我们开始在深夜为“纪念日要不要订餐厅”这种小事吵架。最后一次见面,他把公寓钥匙放在茶几上:“我累了。”
香槟塔突然倒塌的脆响拉回思绪。阿月正被起哄着去抢捧花,白色裙摆在人群里像只白蝴蝶。陈默站在原地没动,手里的酒杯晃出细碎的光。我突然想起上周收拾旧物,在《小王子》里翻出他写的纸条:“如果你要驯服一个人,就要冒着掉眼泪的风险。”字迹被水洇过,晕成模糊的蓝。
散场时陈默追出来,晚风把他的西装吹得猎猎作响。“请柬上的名字……”他声音发紧,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,有些事我没忘。”我把请柬塞进他怀里转身就走,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哒哒响。路过街角花店时,看见玻璃窗里的玫瑰开得正艳,像极了那年他第一次送我的那束。
手机突然震动,是阿月发来的消息:“溪溪,谢谢你来。其实陈默准备请柬时,在你名字那栏改了三次。”我站在路灯下笑出声,眼泪却砸在屏幕上。原来有些人,就算错过了花期,也会在回忆里长成永不凋谢的标本。
夜风卷起地上的梧桐叶,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路口的红绿灯突然变绿,像道通往新生的门。
我攥着那枚烫金请柬站在宴会厅门口时,水晶灯的光正晃得人眼晕。红色卡纸边缘还留着机器裁切的毛边,新郎栏里“陈默”两个字力透纸背,而被邀请人那一栏,“林溪”两个字像淬了冰,硌得我指腹发疼。
伴娘突然从后面勾住我脖子,婚纱裙摆扫过脚踝时带着香氛味:“你可算来了!刚还跟阿月说你是不是要逃婚——”她话说到一半突然卡住,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请柬上。空气里的香槟气泡声仿佛瞬间炸开,我看见她瞳孔地震似的放大浙江配资门户网,“这……这请帖是陈默亲手送你的?”
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。三天前在公司楼下便利店浙江配资门户网,陈默穿着灰色西装站在冰柜前,手里捏着两罐可乐。看见我时他喉结动了动,从西装内袋掏出这个红本本:“下周六,我和阿月。”阳光透过玻璃门斜切在请柬上,把“林溪”两个字照得像血渍。
宴会厅突然安静下来。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从旋转楼梯下来,头纱上的碎钻比星星还亮。我盯着她婚纱后领露出的珍珠项链——那是三年前我和陈默逛珠宝店时,他说“以后要给我新娘戴”的那一款。司仪开始念誓词,阿月的声音带着哭腔:“我愿意。”轮到陈默时,他顿了两秒,目光越过人群直直撞进我眼里。
“我愿意。”
这句话像根针,猝不及防扎进我太阳穴。三年前在出租屋楼下,他也是这样看着我,手里攥着褪色的电影票根:“林溪,等我攒够首付就结婚。”那天的风把他白衬衫吹得鼓起来,像只挣扎的鸟。后来他升了职,应酬越来越多,我们开始在深夜为“纪念日要不要订餐厅”这种小事吵架。最后一次见面,他把公寓钥匙放在茶几上:“我累了。”
香槟塔突然倒塌的脆响拉回思绪。阿月正被起哄着去抢捧花,白色裙摆在人群里像只白蝴蝶。陈默站在原地没动,手里的酒杯晃出细碎的光。我突然想起上周收拾旧物,在《小王子》里翻出他写的纸条:“如果你要驯服一个人,就要冒着掉眼泪的风险。”字迹被水洇过,晕成模糊的蓝。
散场时陈默追出来,晚风把他的西装吹得猎猎作响。“请柬上的名字……”他声音发紧,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,有些事我没忘。”我把请柬塞进他怀里转身就走,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哒哒响。路过街角花店时,看见玻璃窗里的玫瑰开得正艳,像极了那年他第一次送我的那束。
手机突然震动,是阿月发来的消息:“溪溪,谢谢你来。其实陈默准备请柬时,在你名字那栏改了三次。”我站在路灯下笑出声,眼泪却砸在屏幕上。原来有些人,就算错过了花期,也会在回忆里长成永不凋谢的标本。
夜风卷起地上的梧桐叶,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路口的红绿灯突然变绿,像道通往新生的门。
金港赢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